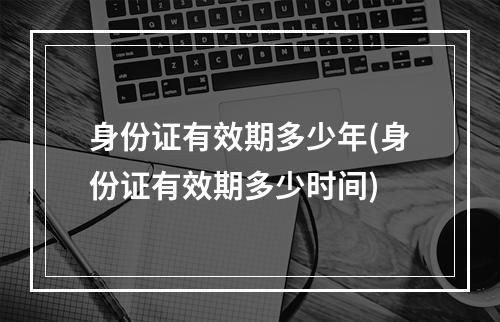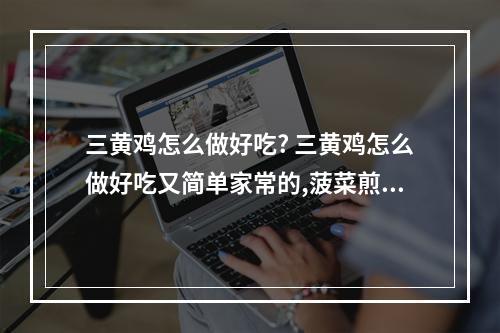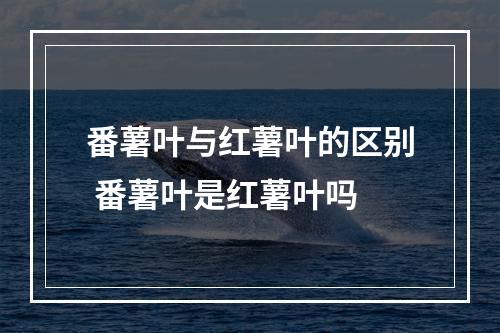公元前三千纪是什么时代(公元前三千纪是多少年)

公元前三千纪是多少年
公元前第三千纪指的是从公元前3999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个时间段。公元前3100年左右,埃及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我国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居住着上万个部落,进入了三皇五帝时期。公元
艺术开卷|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和影响
自19世纪亚述学兴起之后,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长达百余年的研究,让西方人在经历知识和信仰的文化震动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起源,重新认识古希腊、希伯来文明与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而近年来,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展也在国内多地与观众见面。
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出版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一书聚焦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对外传播与影响。本文通过在实物上比较相似的艺术主题,讲述在波斯征服前,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和影响。
从公元前三千纪到约公元前1500年
在希腊铜器时代(Helladic period)的早期(约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希腊和安纳托利亚出现了大致上为圆锥形的陶制印章,通常下部为圆形,刻有简单的几何图案。它们很可能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锡安那(Susiana)平原和幼发拉底河上游河谷广泛使用的记账筹码有关。如果像很久以前猜测的那样,希腊的锥形印章表明“几个世纪前......从东方传承过来的一种传统的留存”, 那么,这些印章就是以宫廷为中心的经济体所需要的记账制度的前身,它们可能是由往来于(泛指的)近东和东地 中海之间的商人在传递知识时触发的。
在幼发拉底河边的西帕尔和底格里斯河中游的阿淑尔的两座坟墓里发现了多个铜或青铜制成的“肚脐形”平底锅,每个锅中央都有一个隆起的浮雕,还有隆起的同心环和长手柄。它们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城市里常见的简易式“煎炸平底锅”有关。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包括特洛伊城的 IIg 层发现了相当多的带浮雕和环的平底锅。这些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2250 年之间,清楚地表明这些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专门货物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地区,该地区正是希腊语民族后来的所在地。
出自阿淑尔一座古墓的带“肚脐”的青铜平底锅,长 0.52 米。特洛阿德也有类似的平底锅
在东地中海发现了两处铭文,上面出现了纳拉姆—辛,即埃什嫩那和亚述的国王的名字。据说,其中一块是 1894 年左右在基西拉(Kythera)岛 的一块白色石头上发现的,但现在找不到了:“为了他的生命,伊佩克—阿 达德(Ipiq-Adad)的儿子纳拉姆—辛向他的主人杜尔—里木什(Dur-Rimush) 的米沙尔(Mishar)神献祭于此。”塞浦路斯的库里翁(Kourion)遗址有一枚印章,刻着这位纳拉姆—辛的一个仆人的名字。这就是纳拉姆—辛国王,他不光在约公元前 1950 年统治了埃什嫩那,而且是亚述的国王。他自封了至高无上的“四方之王”头衔,这就说明他征服了广大地区,一生都被奉若神明。他的征服使埃什嫩那可以在叙利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做贸易, 通过这些地区纳拉姆—辛可以与爱琴海世界接触。但是,这两处铭文都有可能是很久以后作为祖传宝物来到西方的,所以它们不能成为这一时期的可靠证据。
在爱琴海发现了许多滚筒印章,上边有古巴比伦(公元前两千纪初期) 或米坦尼(公元前两千纪中期)风格的图案。它们来自希腊迈锡尼遗址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遗址。虽然这些印章到过很多地方,它们的外观设计在黎凡特常常被重新刻画,但是它们仍使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形象现身于爱琴海地区。
能充分证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曾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有过接触的书面证据,主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址,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玛里发现的皇家档案里的楔形文字泥板曾提到克里特岛人,这些泥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800 年左右。按照这些泥板文字的记载,克里特岛的商品被运送到玛里和巴比伦的宫廷里。在玛里还发现了克里特人的酒器和武器,其外壳常镶嵌着宝石和贵金属。有一段文字写道,克里特岛的鞋子送给了巴比伦的国王汉谟拉比;还有一段记载说,克里特人的船(或一艘船的一个模 型)是在玛里建造的。更多文字说明,乌加里特的克里特岛商人的一个监工和翻译一起工作,参与美索不达米亚与爱琴海地区的贸易。在乌加里特出土的文物已经证实,乌加里特有克里特岛商品。在卡尼什发现的文献记载说明,在安纳托利亚中部,亚述的许多贸易殖民地至少延续到公元前 1800 年,亚述人很可能在叙利亚北部也有类似的贸易殖民地。克里特岛科尼亚(Konya)和斐斯托斯(Phaistos)附近的卡拉胡尤克(Karahuyuk) 村的锁具上的印章,显示了这些行政管理制度之间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可能是在与亚述贸易的影响下产生的。
A. 出自库尔特佩(kültepe)的古亚述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泥板;B. 来自克诺索斯的线形文字 B 迈锡尼希腊语泥板
在黎凡特,比如在毕布鲁斯和阿拉拉赫,人们使用泥板楔形文字,这表明,在这一时期,线形文字 B(希腊迈锡尼时期用于书写)的前身—— 仍未破解的线形文字 A,可能是受近东影响在克里特岛发展起来的。亚述商人使用简化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它由大约 68 个符号组成,大部分是简单的音节符号,在泥板上从左到右书写,通常用画线来换行。线形文字 A 也在泥板上从左到右书写,用画线来换行,由大约 100 个符号组成,大部分是简单的音节符号。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线形文字 A 和线形文字 B 的泥板都在阳光下晒干。这些书写方法可能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到克里特岛和希腊迈锡尼地区。支持这种影响的理由主要是,据我们所知,正如需要印章和文字的城市和宫廷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出现要先于爱琴海一样,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爱琴海之前就有了印章和文字。
青铜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500—前1100年)
在这一时期的前期,克里特岛和希腊的宫廷处于全盛时期,它们有自己的建筑、制陶、宝石和金属加工等工艺技能和传统,它们都摆脱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但是,可以从文字中找到其他影响依然存在的证据。这时, 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写就国际协议的做法,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到近东的所有地区,包括埃及。
叙利亚北部对地中海东部各民族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中心一直很重要。从乌加里特的档案里发现的一份公元前 13 世纪阿卡德语文献明确提 到与克里特岛的贸易:“从今天开始,乌加里特国王尼柯梅帕(Niqmepa) 的儿子阿米塔姆鲁(Ammistamru)豁免了西吉努(Siginu)的儿子锡那拉 努(Sinaranu)。......他的船从克里特岛来这里时被豁免。他必须把礼物带给国王......”迈锡尼的陶制器皿主要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区发现,但在内陆或安纳托利亚东部很少发现。公元前 14 世纪末或前 13 世 纪初在土耳其南部的卡什(Kas)附近的乌卢布伦(Ulu Burun)沉船部分地表明,国际交流可能发生过,因为这艘船载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叙 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地区的货物。但是,在希腊和爱琴海地区发现的可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又不易腐烂的人工制品都是一些小物件,如珠子、吊坠、匾牌和滚筒印章,它们可能间接地由塞浦路斯或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中间商带到爱琴海地区。这尤其从约在公元前 1220 年位于皮奥夏(Boiotian)的底比斯(Thebes)的富丽堂皇的迈锡尼建筑物中发现的一批密藏滚筒印章可见一斑。虽然这些印章的雕刻图案是美索不达米亚的, 但有几个是按照塞浦路斯当地风格重新雕刻的,说明塞浦路斯在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的网络中是重要的一环,但这几个印章对当地的印章图案几乎没有影响。与之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克里特岛艺术对西亚如阿拉拉赫和玛里的壁画的影响。叙利亚的布拉克山丘有一个透镜形状的印章, 其上的花纹图案无疑受米诺斯文化晚期雕刻风格在形状和花纹上的影响, 漫画般地显示了一头母牛的三个生命时期:食草,产子,哺乳。
A. 在乌卢布伦沉船处发现的带象牙铰链的黄杨木文字板,公元前 14 世纪;B. 约同一时期出自哈图沙的铜杆笔
近来,特洛伊城发现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书吏印章。由于书吏可能以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手册为材料学习卢维语,这一时期的卢维语也用楔形文字书写,所以,结合下面的证据来看,卢维语出现在如此之远的西部地区富有深远意义。在士麦那附近的卡拉贝尔(Karabel)山口高处有一块岩石浮雕,显示了一位赫梯国王装束的君主在用象形文字写卢维语。 他可能是图特哈里四世的封臣,其身份是米拉(Mira)的塔尔卡萨纳瓦(Tarkaššanawa)国王,他的装饰着银浮雕的印玺铭刻着卢维语的象形文字和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现在看来,他统治的国家位于迈安德(Maeander) 河以北,控制着从安纳托利亚腹地向西到米利都的主要道路。皮洛斯 (Pylos)城的线形文字 B 泥板和楔形文字的赫梯语文献中都提到过米利都城,来自米利都的女工匠在皮洛斯城工作过,尽管该城在离希腊**西海岸很远的地方。皮洛斯城的迈锡尼国王的某个兄弟在米利都生活过,虽然图特哈里四世在位时迈锡尼人可能失去了该城的控制权。
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山丘发现的米诺斯风格印章
很久以来,用楔形文字写成却在埃及发现的阿玛尔纳书简说明,巴比伦、亚述、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和埃及王国之间的联系很紧密。信使频繁地行走在各个都城之间,王室之间通婚,而且交换过许多珍贵的礼物。 随着我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赫梯的地理,这些信函中记录的各种关系也越来越广泛。在赫梯首都哈图沙发现的书简和官方记载都印证了这些关系的范围。根据法老用楔形文字写给阿尔萨瓦(Arzawa)王国的国王塔洪达—拉 杜(Tarhunda-radu)的信简,我们可以推断,受过阿卡德语纯文学培训的书吏经常游走于各个宫廷,尽管塔洪达—拉杜的书吏说,他认为赫梯语比阿卡德语容易掌握。现在,可以有理由确信,阿尔萨瓦王国的首都阿帕沙司(Apasas)就是爱奥尼亚的一个沿海大城市——以弗所(Ephesos) 古城。 无论阿希亚瓦国王和阿尔萨瓦国王是否收到过赫梯人或阿卡德人的信简,按照传统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教学大纲学习的书吏都在他们的宫廷里出现过。阿卡德语和赫梯语书面语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赫梯早期的王室铭文,传统上用阿卡德语和赫梯语两种语言的楔形文字来写。 所以,这些信简清楚地表明阿卡德语手册里的知识传播到了安纳托利亚的西海岸。我们从阿玛尔纳地区发现的泥板中知道,给国外写信并翻译外国来信的书吏精通传统的文学作品,如阿达帕神话、内尔伽勒和埃列什基伽 勒(Erishkigal)神话。在哈图沙,书吏非常了解三种不同语言的《吉尔伽美什》和阿加德国王的传说。
A. 士麦那(伊兹密尔)附近的岩石雕塑,上有赫梯风格的米拉国王图像和卢维语象形文字的遗迹, 公元前 13 世纪;B. 同一国王印章的银浮雕,上有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和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
这样的知识被传播到渴望改善国际关系的统治者的王宫,清楚地说明迈锡尼时期的希腊权力中心深受巴比伦学术传统的影响。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随之而来。法老的一封来信要求塞浦路斯国王给埃及派遣鸟类占卜专家,这种占卜在美索不达米亚已很普遍,也被赫梯人采用,后来编成书面手册,如《泥板征兆集》。
铁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100—前900年)
在希腊,迈锡尼宫廷里可能只有书吏之类的人才从事文字记录,所以文字似乎灭绝了,虽然在塞浦路斯一直存在。到后来,塞浦路 斯人和安纳托利亚人可以根据假定的青铜器时代国王的血脉,声称与亚述人有亲属关系,但这些文字资料未必记录了他们的历史关系。
然而,考古中出土的文物建起了可以观察这一时期的框架。到公元前 11 世纪后半期,腓尼基人继承了迦南的沿海地区,重新建立了希腊**与近东之间的通商网络;这一网络在沿海地区受到的损坏不像以前想的那么严重。这使希腊人接触了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并最终采纳了这种字母,随之而来的还有训练有素的书吏,他们掌握了很久以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有的学术训练方法。像青铜器时代一样,这个新网络也延展到美索不达米亚, 因为这正是中亚述时期,特别是提格拉—帕拉萨一世(公元前 1115—前 1077)等伟大国王的鼎盛时期;提格拉—帕拉萨一世在幼发拉底河上游附近的安纳托利亚征战,抵达黎凡特的腓尼基沿海城市,收受过毕布鲁斯、西顿和埃及君主送的礼物。在阿淑尔—丹(Ashur-dan)二世(公元前 932— 前 912)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亚述将其帝国向西扩张;协定以及其他契约的谈判起初以阿卡德语进行,配备有翻译。亚述国王富丽堂皇的宫廷对专门的商品制作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又因为希腊人,尤其是优卑亚岛上的希腊人在这一时期的黎凡特地区积极经商, 所以,他们肯定了解美索不达米亚贡献的智慧财富和物质产品。
出土于莱夫坎迪的金项链
考古证据尤其把优卑亚岛与美索不达米亚或与美索不达米亚影响下的贸易联系起来。在优卑亚岛的莱夫坎迪,一座公元前 10 世纪的古墓随葬品中,有一条坠着细颗粒挂件的金项链,“完全和约公元前 2000 年巴比伦的金项链吻合”,所以它可能很久以前就到了优卑亚岛,尽管这种类型的项链和来自叙利亚的项链之间也有同样多的共通之处,而莱夫坎迪的这条项链可能正是来自那里。已知桑葚状三叉金耳环的形状最早起源于亚述,尽管叙利亚北部也用这种金耳环。同样有说服力的还有来自尼尼微的纳布神庙遗址上的一个原始几何图案的陶瓷杯碎片,虽然其外形并不突出,却属于典型的优卑亚岛风格,其装饰是从杯嘴上悬垂下来的一系列半圆。
出土于莱夫坎迪的金珠宝,在设计和技术上有美索不达米亚元素
青铜器时代末期,在阿玛尔纳书简中称为达努纳(Danuna)的民族, 也是埃及人有关海洋民族的记载中称为达奴(Denyen)人的民族,从西里西亚的阿达纳(Adana)来到这里。公元前 8 世纪中期,阿达纳东北部的卡拉泰佩有篇双语铭文,用拼音文字的腓尼基语和象形文字的卢维语提到摩普索斯(Mopsos)“家族”。摩普索斯是个常见名,线形文字 B 和赫梯文 献中都有;因此不能据此推断西里西亚在黑暗时代以前就有很多说希腊语的人。但是,西里西亚的主要遗址上出土了迈锡尼和铁器时代的希腊陶器; 从青铜器时代末到公元前 8 世纪,这里一直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后来, 可以几乎肯定地说,在阿淑尔巴尼帕时期,这一地区有爱奥尼亚人。尽管人们常激情满怀地提出《伊利亚特》中的达奈—希腊人(Danaoi-Greeks) 与近东文献中的达努纳之间,或《荷马史诗》中的预言家摩普索斯与西里 西亚的摩普索斯家族之间的历史联系,但现在看来这种联系未必可能。
优卑亚半岛绘有悬垂半圆形图案的杯子,在尼尼微的纳布神庙、提尔和加利利都发现了这种陶器
西里西亚及其大城市阿达纳、塔尔苏斯、梅尔辛(Mersin)和科伦德 瑞斯(Kelenderis)从青铜器时代挺过了艰难时期,到铁器时代一直保持繁荣兴旺。西里西亚仍然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但阿达纳博物馆里的滚筒印章说明了许多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些印章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三千年末到阿契美尼德时期,按照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 和叙利亚风格设计,混杂着埃及和塞浦路斯花纹。
新亚述时期(约公元前 900—前 612 年)
传统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希腊人与亚述人的接触是敌对性的。 他们认为,由于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和撒缦以色三世在公元前 9 世纪向西入侵,阻碍了贸易,所以黎凡特缺少希腊的考古材料。这种解释遮蔽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仅从两个无效的普通印象汲取灵感。第一个印象就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亚述的战争机器残酷地对抗邻近地区;这个片面的观点基本上已被取代。第二个也是传统观点,即认为希腊人是海洋民族,实行民 主政治,与东部**政权不和;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希腊诸城邦也是被僭主或国王统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海上政权。
然而,一些残缺不全的楔形文字资料提及,希腊人在黎凡特沿岸某些地区进行海盗袭击,所以亚述士兵对他们采取武力行动。记录希腊与亚述冲突的许多楔形文字资料可追溯至公元前 8 世纪末的萨尔贡二世时期,大部分资料可能说的是同一场战役,所以不能据此认为亚述与希腊之间大体上是冲突的关系。萨尔贡时期的亚实突王“爱奥尼亚人”亚玛尼(Yamani)的名字反映了非利士人对希腊血统的自豪感。他们的早期文化中有许多迈锡尼的特征 。
石碑上,亚述国王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的手指指向远方,石碑高 2.18 米;B. 在土耳其发现的萨穆— 拉玛特的石碑,高 1.40 米
公元前 696 年,辛那赫里布派军队到西里西亚平息叛乱后,贝罗索斯说他“按照巴比伦的形象”重建了塔尔苏斯。亚述文献中有再现巴比伦的建筑主题,说明贝罗索斯使用的资料是基于原始记载的。辛那赫里布在一处神庙里安装了一座亚述风格的塔尔苏斯的桑顿(Sandon)神雕像, 该神从赫梯时期以来就相当于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来自塔尔苏斯的罗马硬币表明,桑顿神在哈德良时期仍被顶礼膜拜;亚述人撤离后,当地人没有拆除这座雕像。直到圣保罗生活的时代,当地人仍对该神相当崇拜。楔形文字资料清楚地表明,辛那赫里布所关心的是不断地向亚述进贡,而不是减少安纳托利亚南海岸希腊人的活动。这与在塔尔苏斯出土的文物并不 矛盾,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考古序列断层。希腊人还记得辛那赫里布在战场上留下了一座自己的雕像以纪念胜利,他还命令用“迦勒底”文字铭刻他的勇敢和英雄事迹来启示未来。无论这位国王的名字是否正确,该雕像都可能是亚述帝国为标示亚述利益而建立的著名石碑之一。这可能是几世纪后目击者所说的由“萨达那帕拉” (Sardanapalos)竖起的同一块石碑,该词是王室人名阿萨尔哈东和阿淑尔巴尼帕在希腊语中的变体,这两个名字在传说中被提及时,往往糅合了其他亚述王的传说故事。按照斯特拉博的记载,该石碑上刻有石像,右手手指显示“捏在一起”,他将亚述字母铭文译为希腊语:
阿那金达拉薛斯(Anakyndaraxes)的儿子萨达那帕拉一天之 内修建了安科阿勒(Anchiale)和塔尔苏斯。吃吧,喝吧,快活吧, 因为其他所有事情都不值得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意思是打响指。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os) 为该铭文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并说迦勒底铭文被翻译成了希腊语。
A. 来自萨摩斯的青铜姆舒休龙,高 0.105 米;B. 来自亚述的帕祖祖小人像,公元前 7 世纪,高 0.146 米
C. 贝斯的埃及塑像;D. 乌加里特滚筒印章上的贝斯,青铜器时代末期
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叙利亚和黎凡特相遇。出土文物表明,叙利亚的北部沿海地区是世界性大都会,部分原因是从这里经由奥龙特斯河可以方便地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但是,考古学家重视这一地区特别是阿尔米纳城的同时,不应忽视叙利亚更南部其他港口的重要性,因为直到 20 世纪初,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沿海港口都在为通向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贸易通道提供给养。
贝罗索斯提到过一个传统,说辛那赫里布“在雅典修了一座神庙, 立了青铜像,上面刻有他本人的辉煌事迹”。通常认为,这些事迹不会是真的,但只要提起青铜像,就使人想起可能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青铜器,被供奉在雅典、德尔斐、奥林匹亚、罗德岛和萨摩斯岛的希腊神庙里。有些是原先附在家具或容器上的一部分,有些可能是用于许愿的小雕像。萨摩斯的赫拉神庙里有一组表示许愿的青铜器,旁边站着狗,这与巴比伦的治愈女神古拉(Gula)崇拜有关,常以狗为象征。萨摩斯等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狗葬方式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伊辛(Isin)的古拉神殿遗址附近发掘出的公元前 10 世纪葬狗墓地的方式类似。在萨摩斯还发现了一个已遭损坏的姆舒休龙(mušhuššu-dragon)的形象,它起初与埃什嫩那神相关联,但后来被巴比伦的城神马尔杜克所吸纳;公元前 689 年辛那赫里布洗劫巴比伦后,这一形象又被亚述神阿淑尔吸纳。这些物品说明美索不达米亚与萨摩斯有特别紧密的联系。具有近东特色的是,沐浴更衣后的赫拉形象出现在萨摩斯一年一度的祭拜**中,使人回想起巴比伦的新年亚基突节。
荷花和花蕾图案:A. 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王宫的壁画;B. 辛那赫里布的门槛板上的花纹图案, 约公元前 700 年;C. 科林斯式花瓶上的绘画装饰,约公元前 700 年;D. 乌拉尔图青铜上的切割装饰
迈大步奔跑的吼狮:A. 巴比伦的陶制牌,公元前两千纪初期;B. 科林斯式盛芳香油的圆形花瓶上 的绘画装饰,约公元前 700 年;C. 如阿淑尔巴尼帕雕像所示,位于尼尼微的辛那赫里布王宫里的柱基座
在这些希腊神庙遗址上还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滚筒印章。长期以来, 人们推测,亚述的纺织品也被引进到希腊,由此启发产生了一些考究的装饰性饰品,如希腊东部花瓶上的荷花和棕榈叶相间的链条。有人认为,科林斯式陶器上的花纹饰品、玫瑰花结和狮子图案传承了亚述的主题,原始盛香油的科林斯式长细颈瓶的形状可能由亚述的陶瓷形状体系派生而来。在塔尔苏斯城发现了一只真正的亚述瓶子和一只模仿亚述釉彩器皿的瓶子, 后者可能出产于希腊的制造中心如罗德岛,不过,“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工厂也可能生产这种瓶子”。来自希腊**和爱奥尼亚的金制饰品清楚地反映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代表了从亚述王朝早期延续下来的工艺传统在后世的传承。
A. 滚筒印章上表现的是,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在杀害洪巴巴;B. 利马山丘上一座神庙里,青铜器 时代中期洪巴巴的石制头像
C. 来自奥林匹亚的盾牌上的装饰性青铜标记;D. 位于西西里的塞利农特地区 的雕像,珀耳修斯和蛇发女怪,公元前 575—前 550 年
《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出现的巨怪洪巴巴,与出现在梯林斯和斯巴达,以及黎凡特、塞浦路斯和埃及的一系列假面具有关。这些假面具可能是按照美索不达米亚和腓尼基的习俗, 挂在房屋外侧的门道上。也许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帕祖祖(pazuzu)妖魔形象的影响下,面具上的皱纹和怪相激发了希腊艺术中蛇发女怪戈耳工 (Gorgon)的表现形式。比如,西西里岛的塞利农特(Selinunte)遗址上的一座希腊雕塑显示,与吉尔伽美什一样,珀耳修斯(Perseus)被描绘成杀死了类似洪巴巴的女妖美杜莎(Medusa,再注意性别变化)。希腊的假面具也与埃及的贝斯(Bes)神像有关,现在认为,贝斯的名字是阿卡德语“矮子”的意思,可能是在阿玛尔纳时期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埃及,成为肖像画。独眼巨人如波里斐摩斯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上, 赫拉克勒斯所杀死的九头蛇很像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和艺术中的多头动物,而赫拉克勒斯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一系列行动很像早期楔形文字文献中的苏美尔神尼努尔塔的行为,这些行为后来被挪用给内尔伽勒神。
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的歌手所共有的不仅仅是歌唱的主题。希腊的有些乐器如里拉琴、竖琴、琉特琴、鼓和钹也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现代演奏厅里都有类似的乐器。所谓的“毕达哥拉斯音律体系”也是青铜器时代中期在美索不达米亚被正式确立并记录下来的,很可能与相关乐器一起来到了希腊。杨布里科斯认为,平均律是被巴比伦人发现以后通过毕达哥拉斯传到希腊的,但是楔形文字证据并未证实这一论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出版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
(本文摘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出版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一书,本文作者斯蒂芬妮·达利为亚述学者、英国牛津大学萨莫尔学院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作者A.T. 雷耶斯为古典学学者。)
古代埃及的瘟疫与瘟疫叙事
作者:王欢(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瘟疫作为烈性传染病,是困扰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之一。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代埃及,亦曾饱受瘟疫折磨。对古代埃及瘟疫现象较为明确的记载出自医学纸草文献,目前留存于世的此类文献大都发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断代范围集中于公元前两千纪,部分纸草的底本可能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甚至更早。有些文本虽然指明该文献是在古王国某国王在位时期即已存在,但有可能只是后世书吏为营造权威性而假托,这是诸多古代文明文献传统中常见的现象。
医学纸草涉及古代埃及相当广泛的医学实践知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早期埃及学家称为“科学”的医学知识,主要指对具体病症的检查、诊断、治疗和预后,记录了数百种药物处方;另一类是包含使用咒语治病的纸草,常被归类为魔法文献,有学者视其为古代埃及文明的糟粕。但今天的埃及学家已经意识到,必须综合使用这两类文献,以及如宗教、神话和书信等类型的文献,才能够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古代埃及医学思想和实践的内在逻辑。
以艾德温·史密斯纸草为例,这份纸草文献中有八条驱除瘟疫的咒语,反映了约公元前1600年前后埃及人对瘟疫的成因及其医治的认识。在这些咒语中,瘟疫经常被认为是由邪恶的神明、恶魔、人或动物的灵魂带来的。其中,女神塞亥麦特作为战争、破坏以及瘟疫之神,她或她的使者经常带来瘟疫。除超自然力量可以带来瘟疫,自然界的生命也可以作为疫病的载体,如苍蝇。第三种可能带来瘟疫的载体是“恶风”,这说明古代埃及人对瘟疫可能通过空气传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针对不同的瘟疫成因,咒语给出了相应的除疫方法。对于神明带来的瘟疫,同样需要神明将其带走,故而不少咒语都是向塞亥麦特等神明的祝祷。同时,另一些起保护作用的神祇也会出现在咒语中,站在受害者一边,助其免受瘟疫的侵扰。对于自然界中的生命(如苍蝇等)带来的瘟疫,咒语要求对其从室内食物、床铺等多处进行清理。对于“恶风”所传播的瘟疫,施咒者须通过仪式获得与超自然力量连通的能力。相应咒语要求“路过者”仅仅“路过”房屋,避免将瘟疫引入室内。虽然这是巫术性质的咒语,但切断传播途径、将致病因素隔离在外,是人类数千年来应对瘟疫最传统、最基本的有效的方法。
古埃及医学纸草提及瘟疫的方式是描述相关症状,并提出应对方案,故无法与具体某一次瘟疫事件相关联。在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帮助下,有学者倾向于认为,新王国第18王朝阿蒙霍太普三世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390—前1352年)可能发生过一次瘟疫。这一时期,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力达到顶点。阿蒙霍太普三世在位38年,留下了大量历史记录,仅纪念性的圣甲虫就有200多件,其上的铭文主题包括国王与王后婚配、猎牛、建造人工湖等。他还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葬祭庙,以及超过250座留存至今的个人雕像,“门农巨像”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座。令人意外的是,他在位第12~20年间的历史记录是一片空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战争和瘟疫女神的塞亥麦特在这一时期的雕像激增,现存超过700座,比国王本人的雕像还多得多。敬奉带来瘟疫的女神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既然无法征服她,便希望与她结盟,利用她的力量来保护自身。考虑到古代君主报喜掩忧的习惯,阿蒙霍太普三世历史记录沉寂的八年,有可能是瘟疫肆虐所致。在其统治的后半段,瘟疫是否仍时有发生,目前不得而知。另外,他的儿子埃赫那吞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352—前1336年)曾收到一封巴比伦国王的回信,巴比伦王在信中提到埃赫那吞父亲的一位嫔妃死于瘟疫。另一封当时的阿拉什亚(今塞浦路斯岛)国王写给埃及国王(有可能是埃赫那吞)的信中说,瘟疫之神杀死了他们所有的铜匠。这类外交书信从侧面表明阿蒙霍太普三世和埃赫那吞时期瘟疫在埃及和周边区域发生并蔓延的可能性。
埃赫那吞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异端法老”,曾发动废黜埃及传统诸神崇拜、独尊太阳圆盘神阿吞的宗教改革。传统上对改革的原因分析多集中于这一时期王权与神权的冲突。如果考虑到瘟疫的影响,这次改革的发生则可能另有一番原委:为了躲避瘟疫严重的底比斯,埃赫那吞不得不将都城迁至一处没有受到瘟疫影响的处女地——位于中埃及的阿玛尔那城。同时,既然原有诸神不能从瘟疫中挽救国家,国王就需要废弃旧神,在新都建立新崇拜,是为阿玛尔那时代的宗教改革。这次改革失败后,传统宗教复辟,之后的埃及历史文献对埃赫那吞及之后几位短暂在位的法老采取“除名毁誉”、故意遗忘的记载方式,将这一时期国王的统治时间计入相邻正统法老的在位时间中,直到现代人对阿玛尔那城进行考古发掘,方令这场改革事件重见天日。因此,“瘟疫说”为解释这一时期埃及剧烈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不同于“政教冲突说”的路径。
一千余年后,马其顿-希腊人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埃及本土祭司曼涅托受托勒密国王之命,用希腊语写作《埃及史》。这部书稿今已不存,部分残篇保存在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中,如公元1世纪犹太史家约瑟夫斯的《驳阿庇安》等。这一版本的残篇在关于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历史表述中,记载了阿蒙霍太普三世时代曾发生瘟疫事件:国王因清除麻风病人而获罪于神,麻风病人推举了一位祭司(名为“摩西”)为他们制定不敬埃及神和神圣动物、与埃及宗教相反的律法,并邀请曾入侵埃及的喜克索斯人从亚洲返回,与麻风病人一起统治埃及,阿蒙霍太普三世则退避至南方努比亚地区;13年后,国王携其孙拉美西斯归来,将麻风病人和喜克索斯人联盟逐出埃及。罗马史家塔西佗和其他古代作家所记载的摩西率领部众建立新宗教律法并离开埃及的故事,尽管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叙事模式上与曼涅托颇为相似。这种模式继承了将阿玛尔那时代的埃赫那吞及其后几位短暂在位的君主从历史记忆中抹去的做法,并将埃赫那吞发动宗教改革的13年一并划入其父阿蒙霍太普三世名下。但即便如此,其中的具体情节明显与阿玛尔那时代而非阿蒙霍太普三世时代相对应:埃及祭司摩西带领麻风病人和喜克索斯人占领了埃及13年,这与埃赫那吞实际主导宗教改革的时长基本一致;摩西为其追随者创立的新宗教处处与埃及传统宗教相反,这与埃赫那吞的新宗教相似;同时,所谓从努比亚返回埃及的阿蒙霍太普三世及其孙拉美西斯,暗示的是埃及正统宗教和统治者形象的回归——此时早已去世的阿蒙霍太普三世代表过去的正统统治者,而拉美西斯则是“13年”之后,下一个王朝声名显赫的一系列正统君主的名字。两个辉煌的正统时代前后相继,中间由麻风病人和外族入侵者主导的混乱的“13年”,在曼涅托的记载中以最终被驱逐出埃及的方式来处理。
在“文化记忆”理论看来,包括外族入侵、埃赫那吞对传统宗教的废弃等古代埃及历史上那些令人痛心的“创伤”时代会被刻意遗忘,形成一种“加密”的记忆,容易与其他令人不快的事件相关联。希腊化时代的人口流动明显增多,在各族群交流日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犹太人的一神信仰与同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多神宗教迥异,且犹太社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势力不断上升,经常引起周围其他族群的嫉妒和敌视,在埃及亦是如此。于是,阿蒙霍太普三世时期发端的瘟疫事件虽被长期“抑制”,却从未被真正遗忘,在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记忆中呈现出新的样态:沾染麻风病的人、来自亚洲的入侵者喜克索斯人、不敬传统诸神的“异端法老”埃赫那吞,与希腊化时代对犹太人的早期厌恶情绪相遇,这一切杂糅成曼涅托笔下一段时空错置的记载,并经约瑟夫斯等古典作家的转述,成为将犹太教中的摩西与埃赫那吞或其追随者相联系的滥觞,也是弗洛伊德等人论述犹太教起源于古代埃及宗教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与今天的情况类似,瘟疫同时牵动社会诸多面向,这为我们理解阿玛尔那时代埃及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可能性,以至于关于这一可能性的记载本身亦成为一种涉及犹太教起源的叙事传统:摩西率领一群罹患瘟疫的人,与古代埃及新王国历史上一段持续时间约13年之久的**和宗教改革事件密切相关。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埃及的瘟疫记载不仅是医学史,而且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2022年03月21日14版)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