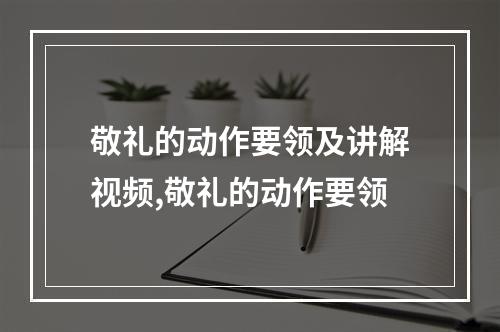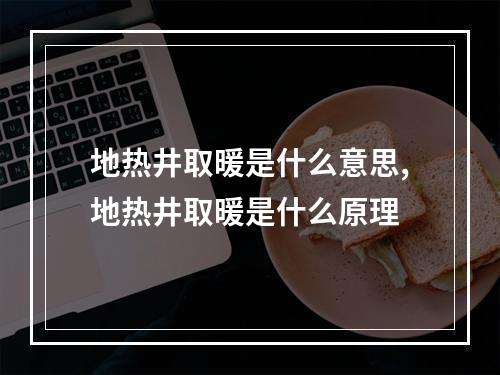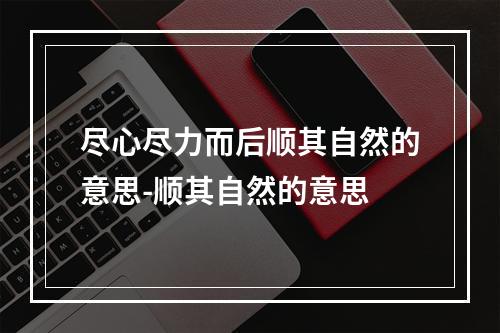如何判断遗传(如何看待遗传性性吸引这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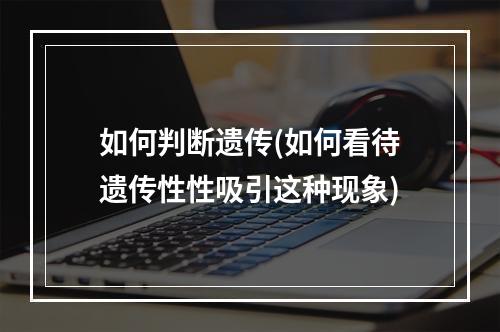
如何看待遗传性性吸引这种现象
人们对与自己长得相似的人更有好感,觉得对方更有吸引力,也更值得信赖。人们在寻找配偶时,也喜欢寻找兴趣相似、个性相投的人,而有血缘关系的人在性格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现象。在父母与子女发生遗传性性吸引时,父母往往会把子女当成自己的配偶来爱,孩子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极有可能遗传了配偶的特性。
“有情人终成兄妹”?拥有1000名子女的超级捐精者引**理难题
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基本都遵循着一个相同的行为准则,那就是避免近亲交配。
即便是在不清楚近亲交配会带来危害的过去,全球各地的人类就已经统一了战线,将luanlun视为禁忌。
这就像是一种古老的本能,而非文化构建结果。
别说是人类,就是在文明没有发生的动物界,也普遍存在着各种避免近亲繁殖的育种策略。
然而,在人类社会中,随着现代助孕技术的诞生,我们也陷入了新的伦理困境。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诞生。
到现在,各种助孕技术已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当然,即便是“科学造人”也需要遵循基本法,“原料”必须是充足的。
如果丈夫精子的质量不过关,那就得依赖人类精子库的援助。
就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男性就可能成为自家孩子的亲爹。
每年都有无数的试管宝宝诞生,给千万家庭带去温暖。
不过,我们也常会幻想这么个可怕的情景,或许“有情人终成兄弟姐妹”正真实地发生。
在那个精子库管理制度不完善的年代,一个捐精者的“原料”供几十到几百人共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然而,却没有办法可以阻止这些孩子们成大后相遇。
更倒霉的是,这些“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兄弟姐妹,甚至还可能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开花结果。
近亲婚配的代价有多高昂,想必大家也清楚。
在人群中,每个人约携带5~6中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基因。
而在近亲婚配中,隐性突变基因则更易于重合显性化,因而后代患遗传病的概率也激增。
所以对于“意外luanlun”这件事,在西方国家也一度引起了一些受赠家庭的担忧。
在历史上,因为精子库稀缺和管理措施缺失的情况下,超级捐精者可不少。
所谓超级捐精者,指的便是那些多次捐精,并成功使多名孕妇受孕的高产男性。
靠科技的力量,每位男性都有可能让那位“拥有94位子女的印度猛男”自愧不如。
印度男子Ziona拥有39个妻子,94个子女,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能生的男人
一名捐精男性,拥有上百个“生物学意义”后代的新闻,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虽然,养父母有责任告知本人,他/她是借精出生的试管婴儿。
而获得精子捐赠的父母,也应自愿向精子库报告孩子的出生情况。
但是根据回访,这样做的父母并不多,在美国只有20%-40%。
生活在荷兰鹿特丹的IT男艾佛·凡·哈伦(Ivo van Halen),就是在30岁来临之际,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你其实是通过捐精受孕而来的。
在这之前,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纯正的欧洲血统,尽管长相不太欧。
但更惊喜(惊吓)的还在后头。
父母告诉他,已经用DNA序列测试出,他的生物学父亲在荷兰境内就有近60个后代。
荷兰真是个小地方,其中一些人就在哈伦的附近长大。
有些兄弟姐妹,甚至在还不知道与对方有血缘关系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就差坠入爱河这最后一步了。
哈伦(左起第二位)与部分兄弟姐妹的合影
为哈伦父母提供精子怀孕服务的,是荷兰的一个政府组织。
他们保守估计,这世界上可能有多达1000名孩子,来自哈伦亲生父亲的精子。
这位“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来自前荷兰的殖民地南美洲苏里南。
他曾在三个诊所内,定期捐精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
而且这些诊所还会进行跨国服务,欧洲各地可能都有他兄弟姐妹的足迹。
伯特尔德·威斯纳
在历史上,奥地利的生理学家伯特尔德·威斯纳(Bertold Wiesner),一直被认为是“捐精界”最高产的男子。
上个世纪,他就在伦敦开有一间生育诊所,专门帮助不孕的妇女做人工受精。
而自己身为医生,他还会为这些前来求助的父母提供精子捐助的服务。
这些精子共用于300-600名妇女的受孕。
根据威斯纳医生本人的保守估计,他共拥有200个后代。
不过现在,若是能够证实艾佛·凡·哈伦拥有1000多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威斯纳医生就可以撤下史上最强捐精者的名头了。
加拿大人barry stevens拿着亲生父亲威斯纳医生的照片
在那个管理不规范的年代,有些超级捐精者也因“内心不安”而主动联系自己的后代。
艾德·豪本(Ed Houben)同样是位荷兰的高产捐精者。
他就曾因担忧自己的生物学儿女会相恋,经常夜不能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已多次尝试将自己的后代约在一起,举办一些活动让对方互相认识,避免乌龙发生。
艾德·豪本
那么问题来了,超级捐精者那么多,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有情人终成兄弟姐妹”的情况?
很庆幸,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生过捐精后代意外近亲婚配的事件。
不过,与之类似的,被领养后代间的意外近亲婚配倒是真实地发生过。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便是一对德国夫妇Patrick Stuebing和Susan Karolewski。
Patrick Stuebing和Susan Karolewski
他们两人从小被不同的家庭收养,直到24岁和16岁才见面——并迅速坠入爱河。
在这之后,他们便相继诞下了四个孩子,然而其中两个都有生理缺陷。
各国的司法系统对luanlun的宽容度都是不同的,在德国他们就需要面临两年至三年的监禁。
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因为这两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兄妹,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兄妹。
所以说,即便捐精后代间从未发生过意外luanlun的案例,但并不代表这不会发生。
但我们也无须过分担心。
因为在更规范的精子库管理下,超级捐精者已经不会再诞生了。
为了避免日后的伦理问题,世界各国早就规定好供精者标本的使用次数了。
在美国、荷兰一名捐精者的精子最多允许25位女性使用,德国是15个,法国是10个。
而我国关于精子库的管理,也是这么多个国家中较为严格的了。
2001年8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就已明确规:每名捐精志愿者所捐献的jingye标本,最多使5名孕妇受孕。
一旦使用次数满了,就会将该名男性多余的jingye标本销毁。
而且,供精者也只能在一个人类精子库中供精,不得跨库捐精。
此外,用人类精子库出生的孩子,结婚前须做婚前排查。
如果女方是捐精出生,就要查清楚男方的父亲是否有过捐精纪录。
虽然人类精子库会为供精者与受精者信息保密,但这样算下来意外近亲婚恋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在统计学中调查中,在一个拥有40万人的地区里,有25个直系血缘关系的后代,他们近亲婚配概率就可以认为是趋近于0了。
所以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捐精后代婚配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个概率可不能直接这样算。
都说在动物界,避免近亲繁殖有千百种策略。
但在捐精后代中,这种策略很可能是失效的。
关于近亲婚配,1987年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提出,在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天生避免luanlun的趋向,也称“韦斯特马克效应”。
爱德华·韦斯特马克
孩子们从小生活在一起,彼此间就会产生一种“消极性性铭记”,导致他们之间性吸引力下降,甚至互相厌恶。
其中一项证据,就来自近代中国的童养媳制度。
这些小女娃几岁就被送到未来的丈夫家,与自己的小丈夫就亲如姐弟(兄妹)一样生活,等到成年后再举行婚礼。
然而,研究者发现童养媳式婚姻的生育率比普通女性低25%,离婚率更是达普通女性的3倍之高。
明朝时期的童养媳证书
不过,韦斯特马克效应产生也有一个前提,出生后6年内成长环境是个关键时间点。
若这个关键时间点内,两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姐妹不在同一个环境下成长,这种“消极性性铭记”就会消失。
如果女童被收养时的年龄在3岁以上,以后的婚姻生活与普通婚姻就没有太大区别了。
所以说在捐精后代完全不重合的成长轨迹中,这种韦斯特马克效应可能是失效的。
朝夕相对的青梅竹马,总是不如天降来得更怦然心动。
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消极印记消失后的兄弟姐妹间,很有可能还会迸发出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这被称为遗传性性吸引(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一般多发于成年后第一次相见的兄弟姐妹间。
人们对与自己长得相似的人更有好感,觉得对方更值得信赖。
只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真实发生的现象。
现在这个理论也只被认为是一个心理学领域的轶事,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所以总的来说,这些都不是目前捐精伦理需要特别关心的问题。
更值得让人担忧的,还是那些盈利性的私立助孕机构,尤其是国外的此类机构。
那些号称能挑选未来孩子皮肤、发色、瞳孔颜色等的花哨宣传,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伦理问题。
如果选择的是正规机构,则基本不必担心此类意外的发生。
现在我们只需要祈祷,那些几十年前管理不规范的超级捐精者的后代,能够不要相遇或者相爱。毕竟现在这些孩子已经到适婚年龄了。
*参考资料
Mark Bridge.Son of ‘super’ sperm donor learns he has 1,000 siblings.The Times.2018.09.29
Guido Pennings.Incest, gamete donation by sibling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netic link.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2001
Martin Fricker.Grand daddy: Sperm donor scientist may have fathered 1,000 babies at clinic he ran.Mirror.2012.12.03
Ross Clark.Sperm donors and the incest trap.The Spectator.2018.08.25
非言语.人为何不luanlun,文明还是天性?.果壳网.2012.01.04
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Wikipedia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
有情人终成兄妹并非空穴来风,动物行为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奇妙
“有情人终成兄妹”是活跃于很多影视剧甚至文学作品的桥段。无论是最为我们熟知的武侠剧《天龙八部》,还是曹禺著名的剧作《雷雨》,甚至外国电影《星际大战》中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
或许你一直认为这样的剧情很狗血,但其实这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梗那么简单,现实往往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20世纪末有一位叫做芭芭拉·冈尼娅的妇女,当她与她那婴儿时期被抛弃、后来长大成人的26岁的儿子重聚时,竟被自己头脑中的淫欲吓了一跳。
后来她提出了“遗传性性吸引(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这个概念,用以描述亲友之间如兄弟姐妹,表兄妹或父母和成年后再次相见的子女之间的相互性吸引。
英国报纸曾刊登过一则母亲和孩子恋爱的新闻
但大多数人却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因为我们身上所发生的“烙印现象”克服了遗传性性吸引。所谓烙印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动物与人类的认知行为模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我们要从动物行为学的祖师爷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以及他的“大雁鹅认亲”实验说起,他因此共享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或许你听说过小鸭子会将它破蛋而出时看见的第一个生物当作自己的妈妈,《猫和老鼠》中的汤姆猫因此得到了自己的“鸭孩子”。虽然汤姆屡次尝试吃掉它,它仍然称汤姆为“全世界最好的妈咪”。
而劳伦兹很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发现禽类幼雏不仅能够在孵化后迅速地与母亲建立亲密关系,而且能够区分自己的母亲和其他的成年个体。但是若孵化后母亲不在身边,它们也会对其他物体产生依赖。
禽类奇怪的认亲行为激起了劳伦兹的兴趣,难道它们是根据睁开眼后看到的移动生物来判断父母的吗?于是他拿来一大窝鹅蛋,快要孵化的时候,他将一半的鹅蛋放在鹅妈妈的窝中,把剩下的放在孵化器里孵化,确保自己是刚孵出的小鹅遇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
结果正如劳伦兹所猜测的,自然孵化的小鹅会很正常地跟着它们的妈妈,而孵化箱孵化的小鹅则总是跟着他。当劳伦兹试图把自己的小鹅与鹅妈妈放在一起时,小鹅并不接受真正的鹅妈妈。
劳伦兹和他的小鹅
接着劳伦兹做了进一步验证。他把所有的小鹅放在一个翻过来的盒子下面,让它们混合在一起。当盒子被移走后,这些小鹅并没有受到影响,它们分别去找各自的“妈妈”——一半去找母鹅,一半去找劳伦兹。
由此可见,幼雏对“妈妈”的认识确实是受着某种影响,它们似乎在最初见到的移动物体上标了印记,此后便会一直跟着这个物体。
其实这就是一种“烙印现象(imprinting)”,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认母印刻(filial imprinting)”,它是指刚获得生命不久的小动物会追逐它们最初看到的能活动的生物,并对其产生依恋之情。
烙印现象是生物的一种生存本能,无疑是有利于生物生存的。它保证了新生群体的安全,幼崽觉得它会被母亲保护,同时它们也会学习母亲的学习生存技能和行为特征。
意大利滑翔机飞行员安吉洛·达里戈曾经在他的滑翔翼下孵化出了雏鸟,这些雏鸟不仅在地面上跟着他,而且当他沿着各种迁徙路线飞行时,它们也在空中跟着,由此学会迁徙。
2002年,安吉洛·达里戈指导西伯利亚鹤从西伯利亚向里海迁移5300公里
劳伦兹是第一个进行烙印现象相关实验的人,但是烙印现象的发现却早很多。业余生物学家道格拉斯·斯伯丁(Douglas Alexander Spalding)在19世纪末就发现了这一现象,有趣的是,洛伦茨的导师奥斯卡·海因罗斯(Oskar Heinroth)也曾研究过这个课题。
虽然烙印现象在鸟类身上尤为明显,但是在哺乳动物中也存在这样的认亲行为,而且感官在动物的烙印现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禽类通过视觉识别移动物体,但是小狗和小猫在出生后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不睁开眼睛,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种“烙印”行为。同时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它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嗅觉、视觉和听觉来判断并识别它们的妈妈。
同时劳伦兹指出烙印现象的发生有一个明确的关键期,这段时期动物对外界刺激尤为敏感。1958年汉斯(Hess)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关键期”的存在。他指出,虽然烙印过程最早可在孵化后1小时发生,但最强烈的反应发生在孵化后的12 - 17小时,而在32小时后根本不可能发生。
有趣的是,通过烙印现象,生物能够学会识别自己物种的成员,从而影响他们成年后的择偶偏好。这种现象被称为“性印记(sexual imprinting)”,这是年轻动物学习理想伴侣特征的过程。
我们知道大多数鸟类并不是一夫一妻制,包括一直象征着爱情的鸳鸯,但是有的鸟类却很忠诚。其中一些鸟类在处于择偶的关键时期时,它的第一个配偶就会被印上烙印。在那之后,其他鸟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配偶。即使原配发生意外死亡,这只鸟也不会寻找或接受新配偶。
听起来这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但是有些鸟类却对饲养员起了“色心”,比较典型的就是人工饲养的猎鹰。不过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饲养员竟然同意了这些猎鹰的请求。当然过程绝非你想的那样。
上世纪末杀虫剂DDT的广泛使用导致猎鹰在美国几乎消失,于是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试图通过圈养繁殖来拯救这一物种。但是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当人工孵化的雏鸟达到性成熟时,它们对与同类的交配却表现出很小的兴趣。
我们之前提到过,鸟类可以与人类建立这样一种特殊的联系,这些被捕获的猎鹰就是如此。它们将无毛的两脚兽视为自己的母亲,并最终将其视为极具吸引力的配偶。
于是乎,在20世纪70年代初,猎鹰人莱斯·博伊德(Les Boyd)发明了一款“爱情头盔(love helmets)”,作为一种收集精子的装置,由此实现了猎鹰与饲养员的“跨物种交配”,并在1975年孵出了他的第一只雏鸟。
正在“交配”的猎鹰和饲养员
操作过程也很简单,饲养员戴着有特殊口袋的帽子收集雄鸟jingye。然后饲养员会寻找一个合适的雌鸟,在“交配”时,饲养员将一只手放在雌鸟的背上,代表一只雄鸟的重量,另一只手用移液管,或不用针头的皮下注射器,将jingye射入雌鸟的泄殖腔。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保护者们成功地将这些猎鹰从濒危边缘拯救了回来。截止到2016年,迄今为止,仅在美国就成功放生了6000多只猎鹰。除此之外,从巨大的加利福尼亚秃鹫到小得多的普劳马多猎鹰都受益于此。
当然“性印记”在哺乳动物身上也有体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伦敦动物园的雌性大熊猫姬姬。当她被带到莫斯科动物园与雄性大熊猫安安交配时,她拒绝了安安与她交配的企图,而是向动物园管理员做了一次完整的性展示。
1967年9月,伦敦动物园的姬姬
其实除了跨物种,一些无生命物体也会被动物视为“同类”,进而出现性吸引。劳伦兹曾经用玩具火车载着大箱子,让箱子沿着孵化器周围的轨道运行,结果成功地吸引了这些幼雏。而现在的一些流行理论认为,在无生命物体上留下性印记可能有关恋物癖发展。
由此看来,烙印效应似乎在创造着亲密关系。如果你还记得开头我们提到的“有情人终成兄妹”的梗,你一定会困惑,因为那个时候明明说的是“我们身上的烙印现象克服了遗传性性吸引”。
其实并没有出错,因为作用于我们身上的是一种“反向性印记”,也叫做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这个现象首先是由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在他的著作《人类婚姻史》中提出的。
韦斯特马克效应在许多地区和文化背景中都能观察到,典型的有以色列吉布茨集体社区文化和中国的童养媳习俗,以及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在我国的童养媳习俗中,年龄较小的女孩会被带到未婚夫家里和他一起抚养长大。韦斯特马克研究后发现,童养媳长大后通常很抗拒此类婚姻,就算勉强结婚,他们的婚姻也很少会美满,而且女方的生育率有一定下降。
而在以色列吉布茨集体社区中,孩童们会依照年龄分开,在不同的群体中生活。在有关吉布茨成员的婚姻研究中发现,这些孩子长大后,同一群体成员间结婚的比例仅占3000个案例中的14例。而在这14对夫妻中,没有一对是在出生后的前六年一起被抚养长大的。
吉布茨集体社区的孩子
这一结果不仅证明了韦斯特马克效应的有效性,也表明亲兄妹6岁前的接触是可以降低性吸引的。而与此相反的遗传性性吸引现象似乎为韦斯特马克效应提供了反向论证。
可以说,韦斯特马克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抑制了人类的近亲繁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伦理道德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不需要担心会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产生非分之想。
此外,烙印现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物的行为,也可以让我们更合理地对待动物。有研究表明,在生命的前六周没有人类接触的小狗和小猫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很好的宠物。而前六个月独自饲养的猴子错过了发展社交技能的关键时期。后来,当它们和其他猴子一起被关在笼子里时,它们要么在其他猴子面前因恐惧而畏缩,要么表现得非常好斗。
不过知道的太多也有坏处,或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青梅竹马”这一直被奉为浪漫的爱情,最后究竟是否能够幸福了。
Imprinting. Wikipedia.UKEssays. Anim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Bonding and Imprinting. 2018.11.McLeod, S. A. Konrad Lorenzs imprinting theory. Simply psychology. 2018, Oct 31.T.L. Brink. Psychology: A Student Friendly Approach. Unit 12: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p. 268. 2008.Behold the falcon sex hat, a species-saving hump helmet. Earth Touch News Network. 2016.3.3.Westermarck effect. Wikipedia.